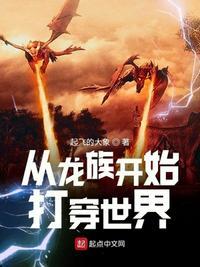笔趣牛>笼中青雀(重生) > 90100(第15页)
90100(第15页)
不过,礼部尚书之言,也的确是许多其他臣子心中所忧。
开疆难,守土也难。
西戎的国土既于大周无用,朝廷也不能强令各地百姓迁去他乡。即便征下西戎,过不上数十年,同一片土地上,又会生出其他异族,窥视中原。
且陛下态度暧昧,今次紫宸殿小朝会,自然没能商议出个结果。
只有“楚王欲征西戎”的消息,立刻在朝中京内传开。
小朝会里的讨论,也或多或少,被心思各异的人,泄露了出来。
很快,下一次朝会之前,一封提议让楚王就藩西陲,镇守边疆的奏章,便经通进司初筛,被送至御案之上。
看过这封奏章,皇帝冷笑三声,直接摔了手中的莲青钧窑盖碗。
“去查!”
他的怒喝与瓷器碎裂的声音,响彻紫宸殿内外数间。
“谁给他的主意——是谁——去给朕查,是哪一个王八蛋!”
第96章第一次失约“不能同你看灯了。”……
奏章的署名是中书省一
名年轻补阙,景和二十六年——才过去的前一年——的进士,不论从二十出头的年龄看,还是从为官的资历以及行事看,都当得上“愣头青”三个字。
高祖皇帝广开言事之路,在京官员七品以上、地方官员四品以上,奏本皆可直达御前。中书省补阙又为谏官,举荐人才、供奉讽谏为其本职,得知朝中议论,他想出这么一个主意上奏,似乎也理所当然。
而想知道他背后究竟有无旁人指使,也很简单。
到了下衙的时辰,大太监陈宝换过一身家常衣裳,带上一个小内侍出宫,找到正走路回家,在街边买饼充晚饭的秦补阙,请他到酒楼里坐了坐。
三杯美酒下肚,几番夸赞递上,秦补阙头也昏昏,意也飘飘,不过几刻钟时间,就将他近日的交际行动吐露了个干净。
“是他同科,户部主事李应兰,还有兵部主事赵自珍同他议论过,是李主事先提起的,让楚王殿下就藩……”陈宝赔着笑回话,“是否比大军西征,或坐待西戎壮大,都更好。”
经过半日冷静,皇帝面上已经看不出怒意。
“李应兰。”他冷哼,又沉思,“赵自珍……”
户部。兵部。
他命:“再查。两人都查。”
……
查了两日,李应兰身上的线索,竟有一条隐隐指向了魏王——宫中德妃的长子,圣人的第四子,现封郡王之爵。
这与皇帝原本的判断大相径庭。
“魏王殿下的伴读若要查,”陈宝为难,“就不大方便轻轻遮住了。”
而赵自珍的行动,最终指向的是永兴侯府霍家。
对于这个还不算结果的结果,皇帝选择接受。
“这点小事,就不必动用皇城司了。”他把面前奏章一推,眼中满是失望,“鬼鬼祟祟,见不得光!有这主意,不敢光明正大来与朕说,只会藏在人后,还要把所有兄弟都扯下岸!”
“不必详查,朕也知道是谁!”他冷笑。
这两日,相同提议的奏章,又有几封飞到他面前,秦补阙是太过冲动,不自觉给人打了头阵。藏在暗处之人,不知还煽动了多少心怀各异的蠢蛋,重提封王就藩之事!
“传朕口谕:今日起,有再重提皇子就藩一事者,便以祸国谋反之罪论处!”
太子——太子要将楚王彻底赶去西疆,无非是怕他已经年老,将来若真有皇位之争,他不能顺利登极!
京中没了楚王,皇子里谁还可与他分庭抗礼?齐王、魏王之母,虽也都在一品夫人之位,但齐王只在修书,魏王不过太府寺卿,他两人的母族妻族,又谁能及得上承恩公府与寇家的权势?
“朕自登位,便立他为太子,多年来,亲身教养,从无苛责。自皇后故去,二十五年未再续娶,又重修太子之礼,以使无人能轻动储君之位。本以为,父子之情必能保全。”
皇帝站起来,行至窗边,推开窗扇,看向大明宫之东:“可朕,才方至半百,他便如此……”
已将傍晚,窗外的日光渐趋稀薄。
东面的天空率先灰下去,西方的晚霞还余最后一丝,也将尽数沉没。
皇帝却觉得,那一抹黯淡的青紫晚霞真是刺眼。
“旁人也未必干净。”
他转回身,背对窗外稀疏的霞光,身体被薄暮笼罩,双眼却亮得惊人。
“楚王,呵,没了朕拘束,他在西疆就天高山远,尽得自由。”
一面走回已被烛光照亮的御案,他一面轻声地,失望地说:“齐王、魏王……有就藩之例在前,他们便也能趁机谋求外封……”-
皇帝震怒的口谕,追着沉落的霞光,一夜之间,就传遍了朝堂内外。
上过奏章的几人无不为之胆寒。有几人惊惧过甚,直接病倒在床,不能起身。
太子也又做了一夜噩梦。
东宫臣属集会,太子伴读庄某,便在一片死寂里愤然开口:“我早便说过,提议楚王就藩,有百害而无一利!”
他正任大理寺少卿,虽然只在三十过半年纪,怒目看向官阶高低不等的同僚,便似在公堂一般生出威势:“陛下若全无征西之心,为何会允楚王朝会提议?又为何不令晏尚书说死户部空虚,反令众臣议论开支?只要陛下之意已决,楚王西征本就无可阻拦!”
“这话且不必再提!”工部尚书寇某摆手道,“陛下若真已决心西征,也不必叫朝臣商讨,又看京中各地的舆论反应了。无论如何,只要事还未定,就不能让楚王再立此功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