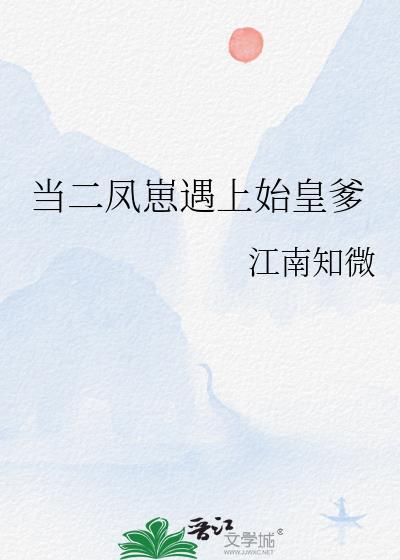笔趣牛>反派对我产生了食欲怎么办 > 第43章(第1页)
第43章(第1页)
她在晕眩中看见站在面前惊讶的钟夫人。
“怎么了沈探员?”钟夫人拿着创可贴的手被她紧紧抓了住。
沈初一在短暂的几秒内心跳得飞快,她说了一句:“抱歉。”慢慢松开了钟夫人的手,随口撒谎说:“我有点创伤后应激,会下意识挡住靠近我的东西。”
她在钟夫人眼睛里看到很柔软的东西,像一个母亲看着可怜的女儿。
“没什么好抱歉的,沈探员是为了救人才受伤。”钟夫人把创可贴放在她手边的洗手台上:“要是能帮到你就好了。”
沈初一拿了创可贴,闲聊一般问:“夫人怎么会随身带创可贴?是您哪里也受伤了吗?”
她看见钟夫人脸上的笑容有几秒地“卡顿”,随后又温温柔柔笑着说:“没有,今天要见福利院的小朋友们,所以特意带的,我曾经在福利院里教过书,孩子们总有不小心的时候。”
撒谎,就意味着那些伤口是不能摆在明面上说的。
沈初一目光扫到她的小腿,她穿了丝袜,裙摆刚好盖住受伤的位置。
摔碎花瓶的、伸手要拉扯她动手的人是谁?是她的丈夫钟康明吗?
门外,有人轻轻叩了叩门:“夫人,活动要开始了,副首相担心您迷路,让我来带您过去。”
钟夫人应了一声,朝沈初一道了别,快步离开了洗手间。
太奇怪了。
钟康明和钟夫人“恩爱”的很奇怪,她忽然出现的“闪回”也很奇怪。
她的“闪回”难道不是在案发现场才会出现的异能吗?
怎么会在碰到钟夫人手的时候“闪回”出这些她被家暴的画面?
沈初一对镜粘好纱布,无端端冒出一个猜想:寄出那封信的人会是钟夫人吗?
可这个猜想没有丝毫根据,甚至很荒谬不合理。
比如:以钟夫人的身份她还需要自己做家务清理地漏吗?
再比如:如果九尾狐案的凶手是钟康明,他为什么要把抛尸在那么明显的地方?把案子闹得这么大?他应该有很多办法让一个人、一具尸体无声无息地消失吧?
荒唐的直觉。
沈初一想自己该改一改自己凭直觉做事的习惯,办案是要靠侦查和证据的,办案不是赌博。
她对着镜子穿好外套,拉开门出去。
※※
距离活动开始只有五分钟了,她匆忙下楼,看见楼梯口站在的白世舟。
他很高,低头在看手环,深灰西服下是笔直的两条腿,银白的头发修得很短,从背后看过去像个男模。
“署长在这里干嘛?”她走过去问。
白世舟朝她了过来,皱了皱眉说:“你是拉黑了我吗?”
沈初一一愣,马上低头看手环,果然看见有一通来自白世舟的未接来电:“没拉黑啊,只是没听到。”只是把他设置成了来电静音而已,谁想天天接到上司的电话啊?
“署长找我有事?”她问。
白世舟有些无奈:“你知道自己的座位在哪儿吗?”
沈初一忽然反应过来,他是怕她不知道座位在哪里,在这里等她吗?
可为什么不直接说呢?为什么要用反问句呢?
她不高兴,直接说:“不知道,但王助理会带我过去,署长等在这里是因为也不知道你的座位吗?我可以帮你问问王助理。”
白世舟愣了一下,就见她绕过自己径直朝王可的方向走去。
他张了张口想叫住她,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座位在哪里,他是在等她,要带她一起过去。
可才张口就听见楼梯上有人轻笑了一声。
他回头看见从二楼下来的章典,“章教授?”章典也在二楼?章典居然出席了这场活动,他不是一向不喜欢这些活动的吗?
“看来白署长和新探员相处得不太愉快。”章典笑着走下来,到他身边好心建议说:“有本书可以推荐白署长看看,叫《说话的艺术》。”
白世舟错愕的站在原地,不明白是不是他的错觉,章典好像在讥讽他?
这又是为什么?
会场的灯依次亮起来。
白世舟回到自己的座位,看着王可亲自把沈探员送到了他身边的座位,笑着和她耳语说了什么,又朝他点点头离开。
她像是在生气一般,并不和他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