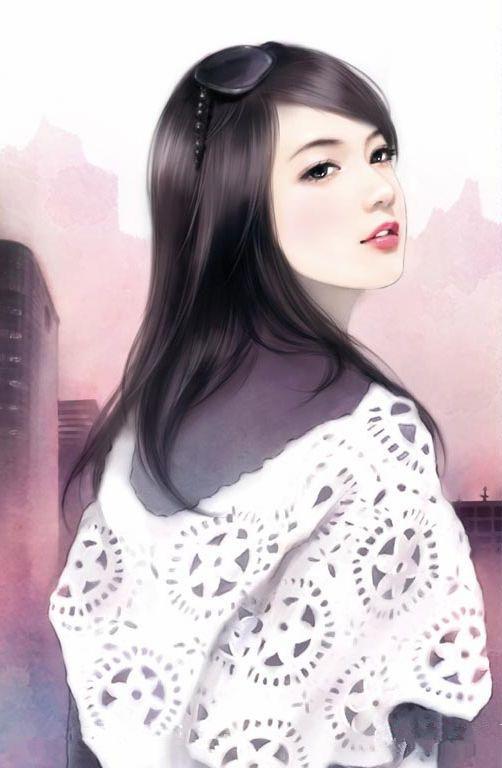笔趣牛>渡魔成圣 > 圣人谢衍 殷别崖你给我回来修(第4页)
圣人谢衍 殷别崖你给我回来修(第4页)
他的体温灼烫,魔气常年犹如烈火,在他的血脉中涌动。
爱与恨,还是生机勃勃的。
这样很好。
谢景行虽然心里明白,那是自己的一部分魂魄,很快就要回到自己身体里,记忆合二为一,心里仍然极不舒服。但是无人能从他幽沉的表情上,看出他心中所想罢了。
他躺在徒弟怀里,他渡来的灵气正在活化身体,让他浑身发热,像是在温泉里。
魔的自愈能力太强,殷无极不怎麽通晓治疗手段,拔除剑意时,哪怕再小心,也会让谢景行冷汗涔涔,痛的脸色发白。
殷无极自知理亏,低声道:“忍不住就咬我。”
谢景行恨他自毁,实在恨的牙痒痒,对着徒弟的脖颈就是一咬。
殷无极侧了侧颈,任由他咬在自己的要害,手中却专注为他拔除剑意。
平日见陛下与谢先生相处,本以为只是移情。可圣人残魂在前,陛下却能优先为谢先生处理伤口,这让目睹他这麽多年疯魔的陆机心里颇觉怪异,甚至有了些许猜想。
“外界如何了?”白衣天魂问道。
“仙门大比,飘凌与游之来了,相卿守宗门。”
“儒道如何?”
“道统零落,亟待复兴。”
“隐忧?”
“成为现实。”
“……他的心魔呢?”圣人天魂看向殷无极,眼底依然雾气蒙蒙,却显得格外的清远。
“变本加厉。”谢景行叹息。
“……不是什麽大事。”殷无极小声反驳。
谢景行冷笑一声,反问:“自毁,不算大事?”
殷无极不答。
他看上去正常,实际上早就疯的不成样子。他时而疯癫如狂,时而清醒冷静;他心机深沉,却展露天真颜色;他喜怒无常,容易厌倦,有时又有莫名其妙的执着。
谢景行甚至会觉得,他心早已成了灰烬,成了冷铁,甚至都不想活下去。
圣人谢衍曾经用尽一切办法,即使是要他以恨为食,也要让他挣扎着求生。
做师父的人,大抵就是这点自私。
“是我之过,我会听您的话。”殷无极的下颌抵在他的肩头,忽然道,“真的,我不骗您。”
圣人原本冷硬的神情,忽的就怔忪了。
“你过得,似乎还不错。”他的眸里似乎有柔软的温情涌动,却又有冰冷肆虐。
长街上涌动的雪与风要他做出抉择,他看向遥远的宫墙,却迟迟无法给出答案。
他最终还是道:“给我些时间,把馀下的事情处理完。”
谢景行当然知道自己要做什麽,道:“好。”
殷无极擡头看了一眼天魂,那似疯似狂的神色消失了。
时过经年,他们最癫狂的时候早已过去,如今的温情,也是在失去後才懂得珍惜。
遗留在过去的影子叹息一声,衣袖猎猎飞扬,仿佛临风而来的仙神。
他归去时,风雪染上墨发,恍如梨花白头。
殷无极搂住谢景行纤细的身子,擡起眼,骤然问道:“圣人,您想做什麽?”
他的口吻,却是温和的,柔软的。
在逝去之前,圣人谢衍已经许久未曾听过他这样的口吻。
圣人天魂的背影一顿,在漫天的风雪之中,放声吟道。
“车辙尽处,岂效穷途而哭,馀一生,困于天道,来时问天路,去时,当斩天而归。”
说罢,白衣身影在风雪中消失不见。
殷无极握着谢景行的手腕力道收紧,眸色绯如滴血。
“他会回来的。”谢景行咳了一声,拭去唇角的鲜血。他从天魂那里得到了不少信息,可身体撑不住了。
在陷入沉睡之前,他教训徒弟的口吻,依旧温柔到可怖。
“殷别崖,等我醒了,我们好好算算帐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