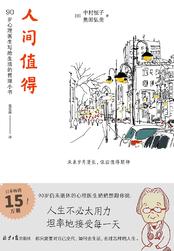笔趣牛>嫁夫兄 > 4050(第3页)
4050(第3页)
他有病吧,他都快接受了。
裴玄章:“逗你玩。”
支知之站起身子追上他,桃花眼一眯,骂了句脏话道:“裴今流,老子就知道!”
他翻身上马,暂时懒得搭理裴玄章。
但想了想又不服气,侧眸慢悠悠道:“我说裴玄章,你这么说不会是因为你自己觊觎谢姑娘,不好意思说吧?”
裴玄章冷笑一声,斜睨他一眼,看他的目光犹如在看一个傻子:
“觊觎她?这辈子都不可能。”
下错刀了。
谢怀珠懊悔的停手,看着手里的木头思索着应该怎么补救。
观察了半天,发现补救不了。
九十文居然就这样没了。
她捏着那块被刻错的木头,烛火印出这块四不像木头的轮廓,半晌,谢怀珠又重新下刀。
她把它改成了一只撅着屁股伸懒腰的小猫,小猫双眼眯起,懒洋洋的。
谢怀珠捏着它看了一会,正好手指有些脱力,她该休息了。
房门忽然被敲响。
谢怀珠回头,皦玉探着脑袋看过来,做贼一样小声的道:“姑娘,有人找你。”
谢怀珠放下刻刀,站起身来问:“谁?”
皦玉声音更小了,几乎只是对她做了个口型:“大,公,子。”
她一字一顿的说。
裴玄朗怎么这个点过来了。
谢怀珠穿好衣服,推开门走出去。
月色空朦,裴玄朗站在她的小院门口。
清透的月光照在他白皙的脸庞,看见她时,男人朝她轻轻弯起唇角。
谢怀珠问:“裴公子,怎么了吗?”
裴玄朗身上有股淡淡的酒气,但他的脸上并无半分醉意,他对她道:“今天那件事,我已经查清楚了。”
他没有跟她细说这其中是谁在嚼舌根,只道:“能查到的,我已经处理掉了。日后倘若还有人说到你面前,你只管告诉我。”
谢怀珠没客气:“好的。”
闻到裴玄朗身上的酒气,她又轻声问:“你喝酒了?”
裴玄朗嗯了一声,同谢怀珠解释道:“今流三年没有回京了,今日都是他曾在京城的一些好友,大多与我也有些交情,就多少喝了一点。”
谢怀珠心想,裴玄章又胡说。
这么说来,同支知之“一起长大,门当户对”的人根本不是裴玄朗,是裴玄章自己。
“熏到你了?”裴玄朗问
谢怀珠摇摇头。
夜风吹过,将谢怀珠身上清淡的茶花香送到裴玄朗面前。
他们面对面站着,裴玄朗这样看着她,明明隔着一段不近的距离,他却似乎仍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温暖与柔软。
像一盏烛火,一寸一寸亮到他心里去。
而谢怀珠半晌没听见裴玄朗说话,心想裴玄朗可能还是有点喝醉了。平日只因为这点事,他是不会专程过来找她的。
“还有什么事吗?”她问的很直白。
裴玄朗笑了起来,笑声很低,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,他摇了摇头道:“没事了。”
“回书房的路上,莫名想到了你。”
“也不知道怎么,就走到这来了。”
谢怀珠:“哦。”谢怀珠回去以后发现房间院落被收拾的很干净。
以前也整洁,但今天着实整洁的有点过分了。
皦玉站在小厨房边小心的看着她,轻声告诉她今早那碗粥被她放在了木柜里,谢怀珠看她这副担惊受怕的模样才慢吞吞反应过来。
皦玉可能是怕她迁怒她。
谢怀珠在裴家地位不高,得处处小心,但裴家有不如她的人,得在她面前处处小心。
就像当初她差点被送官府,彼时那位受伤的官员对她而言是难以撼动的存在,但是裴玄朗轻而易举就化解了,可能裴玄朗对那位官员来说,也是难以撼动的存在。
要这么算下去,恐怕得做皇帝才能真的无所畏惧,但当皇帝真的就无所畏惧了吗?
就像她娘亲,总觉得他们娘俩孤苦无依,在外面得看人脸色生活,执着的想找大家族庇护,但谢怀珠觉得,来到大家族也需要看主母脸色。
倒不如去江湖小镇,靠本事讨生活,这样还自在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