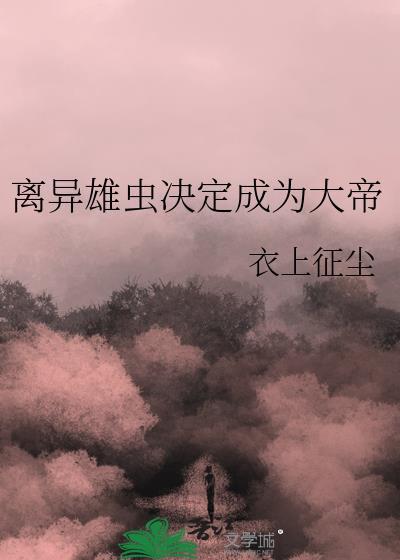笔趣牛>白日飞升 > 第29章(第1页)
第29章(第1页)
听完宣召的内容,她心中大为疑惑,皇帝的意思是要解除她的禁足令,虽不可立即奔赴边关,却要她自明日起照常上下朝。不过她面上不显分毫,恭敬地接过了太监手中的圣旨。待太监离去后,就揣上圣旨找沈拂去同他商量一二。可她找遍了国师府的每个角落,都不见沈拂踪影,不过她也清楚,从小到大沈拂经常有事外出,时常一去就是半个月一个月,所以心里也没想太多,只以为是他又有事出去了。却并未想到,沈拂几乎从不会在深夜外出。次日的早朝上,沈挽舟也知道了,那日跟在她身后的那人竟是当朝三皇子——裴颂。自那日之后两人一来二去,竟也逐渐熟悉起来,裴颂其人,虽然看上去不甚着调,但沈挽舟总觉得此人不似他表现出那般普通,有时候他的一些所作所为隐隐有些帝王之色。不过这种念头在沈挽舟心里也只是一闪而过,她对一些除她师父之外的身旁之人总是不甚关心,她只想护好自己的小家便很好了。之后又是平淡的一段日子。突然有一天早朝上,边疆传来急报,老将军战死,一大把年纪了,也算是静毕生献给了战场。匈奴正敢在此时,公然违背约定卷土重来,现已攻下边关三城,就是之前沈挽舟夺回的那三城。现如今他们正一路向着京城驱进。沈挽舟虽不喜朝堂的勾心斗角,对当前的国家局势却很清楚。如今的梁国可谓是从根子里就已经腐朽,除了她之前驻守边关时训练的那几支军队战力尚可之外,其余各城驻军,恕她直言真的是不堪一击。而如今她被禁足在京的这段时间,最开始军队在那“陈草包”的带领下,连败数场不说,整个军队的风气都被带坏了,战力也早不知退化成了什么样,能抵挡住兵强马壮的匈奴才真是奇了怪了。虽说后来有了皇帝请回的早已卸甲的老将军坐镇,但老将军终究年岁已高,虽然在军中以有威望,但由于军队沉疴已久,老将军纵有经世之才,恐也无能为力了。如今,边防被破,攻入内地直至雍京,说实话,沈挽舟心里真的没底,但偏偏她又做不得什么,皇帝虽说保留下了她的职位,却也只是空有虚名,并无实权。而还有一个事儿令她极其焦虑,沈拂也就是她师父老人家已经出去了足足有三个月了。以往最多一次也只是出去了一个月,近日她的左眼皮还不停地在跳,心里隐隐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皇帝听了探子传来的急报,身子依旧稳稳地坐在龙椅上,神色不见半分慌乱,只是挥挥手让来人退下。虽然皇帝心态很稳,可百官却是直接炸开了锅,有认为要集结全部兵力背水一战的;也有认为要向匈奴投降,并即刻迁都去南方避难的,只是按此说法一来,大梁国土势必要让出大半了。吵着吵着,朝堂上逐渐行程两个派系,以王丞相为首的主战派主张全力镇守雍京,并掉部分驻守南疆和东海的兵力前来支援。而以方太尉为首的主和派,则想着向匈奴递上降表并即刻迁都至江南一带,以求休养生息。沈挽舟更倾向于主战一方,对方太尉那帮人的想法嗤之以鼻,笑话,什么休养生息,说白了不就是懦夫行径打不过就跑嘛。他们倒是一走了之了,百姓怎么办,被他们弃之不顾的北方十六城的百姓怎么办,都要命丧那些蛮子们的铁骑之下了吗。她不甘心。却又无能为力。整个大殿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,只需龙椅上那人表个态。沈挽舟也不急,就这么望着皇帝,说不清楚心里怎么想的,她总觉得皇帝就算比较多疑甚至在一些小事上比较拎不清,但这种家国大事应该不会由着方太尉那帮子人胡闹的。她用着自己都并未察觉到的期待的目光,望向高座上的那人。但随后,心却被狠狠地抛下了谷底。那人说,迁都吧。她不相信,又仔细地听了一遍,皇帝也察觉到了大殿上一瞬间的安静,沉着语气重复了一遍。“朕同意方爱卿的说法,迁都吧。”说罢停顿了一下,又继续道:“杭州便很好,物产丰富,人杰地灵。”沈挽舟确定这次自己听清楚了,皇帝的态度很鲜明了,他主和。说不清楚那一瞬间是什么心理。失望?愤怒?亦或者两者都有。上位者的一声令下,宫里匆匆忙忙的忙碌开了,有些人听到小道消息皇帝要跑,也纷纷开始收拾细软跑路。沈挽舟曾在那天晚上私下里见过一次皇帝,想要顶着杀头的风险以戴罪之身再劝谏一次皇帝,万万不可迁都。